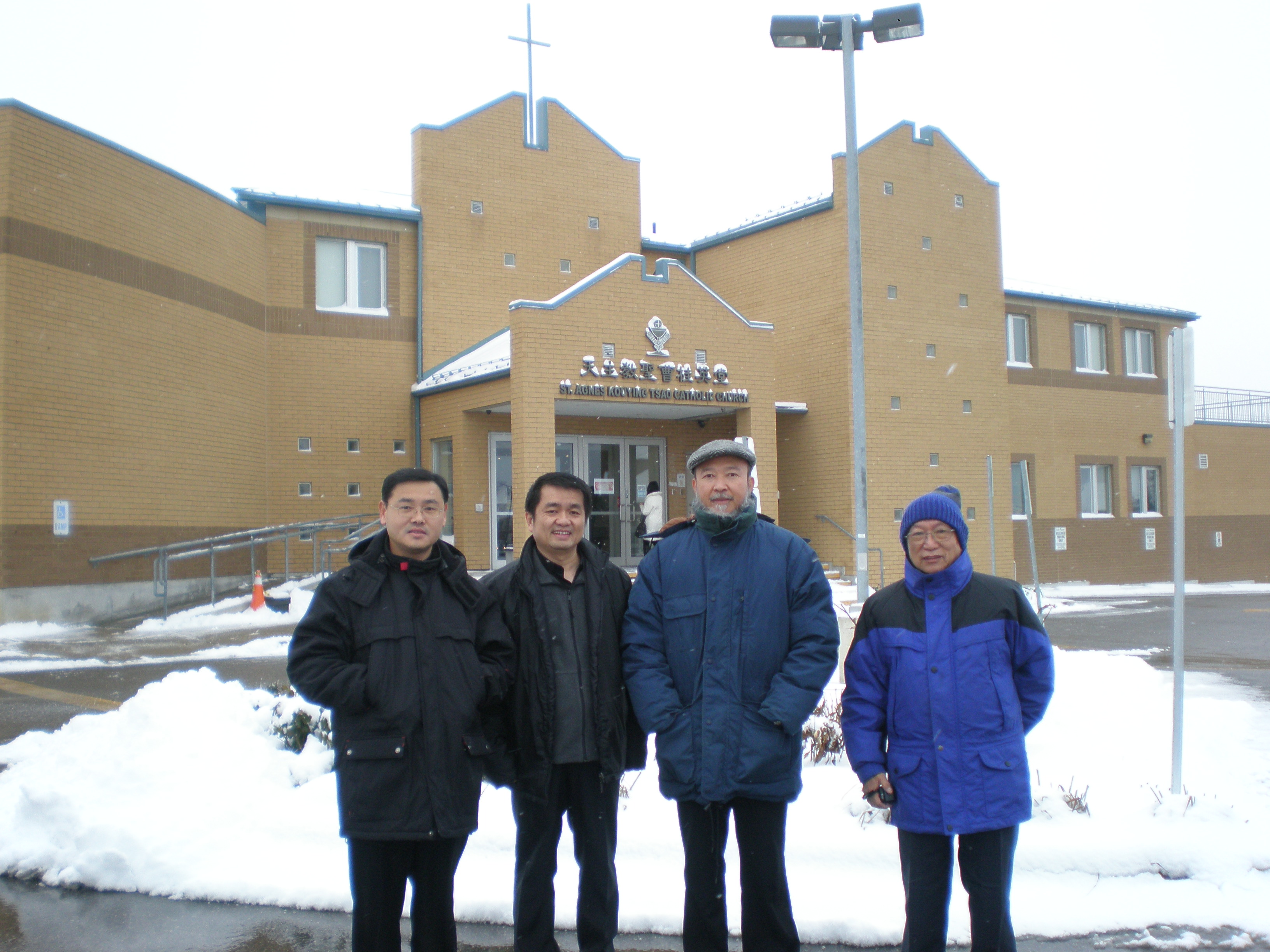心 之 旅 四 季 情 文/黃進龍 一、籃球場上的奔馳 曾有一段時日,在主徒會總會院附近的文化大學打籃球,隨意和場邊的學生組成三人一組「鬥牛」﹙three on three﹚,是我的例行活動之一。我打籃球以運動為目的,不在乎勝負。大學生習慣用「老伯」來稱呼我,但也樂於與投籃有一定準頭的「老人家」搭檔。持平而言,大學生打起球來有很好的風度,但也有些學生「血氣方剛」,常因身體上的碰撞而起爭執,還得由父執輩的我好言相勸:「運動嘛,別太在意!」,替他們消弭怒火。 依稀記得:許多年前的初中時期,與四十來位小修生在聖母昆仲會的聖若瑟初試院接受陶成。那是我第一次離開家鄉,從馬六甲前往吉隆坡求學,也是生平第一次接觸籃球。由於修生的人數眾多,每人上場的機會相對的少,我在球場邊等待的同時,也學會在心中反復練習各種打球的技巧,因而很快就喜歡上籃球。不管是炎熱的午休時間,或是傍晚的運動時間,只要有機會就上場奔馳。 OLYMPUS DIGITAL CAMERA 青澀的少年逐漸步入中年,從八打靈聖若瑟初試院、台南碧岳神學院、馬六甲主徒會培訓院、文冬耶穌聖心堂,到台北主徒會總會院或是其他地方,打籃球成了我在這些地區,惟一相同的嗜好。歷經多年的磨練,無論是籃球或聖召,我對這兩者的了解與體會,已經從過去的渾然不知到今日的自然渾成。 多年的修道生活,再回首這一段路程時,既難從中梳理出明晰的因素,也沒能給個明確的範本。像是「修道聖召與我」、「我的修道生活」或是「我如何回應修道聖召?」等諸多此類的標題,都無法繪出自己心中對修道聖召的體會。無論是廣義的聖召,或是狹義的聖召,莫不都是人循著天主的召喚聲,亦步亦趨地以具體行動加以回應?這當中少不了回應前的猶疑不決、考量再三,讓人難以割捨的世態人情,或許還有些許的自私,甚或回應之後的一些不切實際的憧憬。 天主似乎老早就把「路線圖」擺在那裡,我無意間拿起後,像是一個不知天高地厚的冒險家,未經多少思考就輕裝上路。這般率性也是一件幸福的事,沒有太多的包袱,一路上只有信靠。在球場上沒有太多的跌倒碰撞,或許只是未曾遭遇頑強的競賽對手,也可能是自己應對得當,也許冥冥中有來自天上的助力。 走在修道生活的路上,實在不需要找來外在的對手;先過得了自己的那一關,才有上路的力量,而投靠天主的心,就是最好的指引。如此看來,外在的一切是非與考驗,何嘗不是生活上的調味品?一路走來,「山重水複疑無路,柳暗花明又一村。」 是什麼因素讓人持續上場奔馳?是場邊的掌聲、讚賞的話語和羨慕的眼神?或是汗流浹背之後的活力感?還是其他的因素讓這運動的因子歷久不衰? 構成這畫面的最大推動力,應是由熟悉的環境中抽離,跨向陌生的人群,設法與不同的個體互動,達成共識並組成合作團隊,在愛中來完成既定的目標。這看似簡單的舉動,卻需要一次又一次的嘗試。人與人之間的距離,有時竟比肉眼所看到的遙遠許多! 我的修道生活,堪與球場上的奔馳互作比擬。不斷地走向人群,又返回內心、歸向天主。那是一種看不見的流程,也沒有既定的模式可循。舉手投足間,均流露一股寧靜的力量,像是再熟悉不過的事,卻不斷地有意想不到的驚喜。這當中已有多少人投入他們的愛及心力,才能構成此時此刻的畫面? 我無法答覆。那是我所敬愛的祖父祖母、父母親、黃老師、林老師、張修士……,還有數不清的長者與伙伴。 二、阿依沙叻的溫情 對祖母的記憶,從小至今都很深刻。說不上為什麼,我認為是她對我的信仰生活發揮了深遠的影響。祖母是新加坡「惹娘」,祖父是馬六甲「峇峇」,兩人結婚後即離開富裕的曾祖父,赤手空拳到人跡稀少的阿依沙叻開山闢地,成家立業。一對新婚夫婦,連一間像樣的棲身之處也沒有,卻展開了一段艱辛、簡約的新生活;祖母並沒有埋怨,她試著去順應自然,以優雅的儀態把眾多的孩子一一拉拔、撫養長大。 父母親結婚後,家裡依然務農,常是種些稻米和蕃薯等,這類的農作物所需投入的資金不多,但收入也有限。家裡雖然貧窮,但生活過得有格調。此時的祖母極少下田幫忙,常是留在家裡幫忙照顧孫子。祖父和祖母向來以馬來話交談,偶爾說些客家話,有時也和家中晚輩說潮州話。肩負大家庭生計的祖父,生活樸實,為人嚴謹,常是沉默寡言。午餐後,祖父總會騎腳踏車到一公里外的小市鎮喝咖啡,與友人聊天,這成了他生活中既平凡卻又不可缺少的休閒活動。 祖母擁有一顆慈悲的心腸,常將家裡種的水果送給左鄰右舍的小孩。在物資缺乏的年代,即便是一顆小小的水果,也能讓人回味無窮。她關懷自己的孫子,常將遠方客人送來的水果,拿來和我們分享,舉手投足間,總是使人備感親切與溫暖。祖父母為人向來大方,不喜歡斤斤計較,以信仰的眼光看待事物,也樂於與他人分享自己所有的一切;家裡有一口水井,井水清澈,長年有水。天氣乾旱時,也常見村民前來汲水。 當時,阿依沙叻村內已有上百戶人家,家家是教友,堪稱「教友村」。每天晚上,村子裡各家各戶都有全家人一起念經祈禱的習慣。從村子頭到村子尾,家家戶戶不約而同地傳出誦經聲。祖母是我們家的「領經員」,總會在家人上床睡覺前召集家人一起念經。若有人稍為怠惰或耽擱,祖母就會說:「你們自己聽一聽,某某鄰居都已開始念經了,還不趕快過來!」不論大人還是小孩,即便雙眼矇矓、身體疲乏,總得先把經念了才可以上床休息。 中學整整六年的時光,我在聖母昆仲會的初試院度過。家中成員也陸續出外工作或讀書,能在晚間一起祈禱的家人逐漸減少,但祖母在大廳念晚課的習慣未曾間斷。後來,祖母的健康逐漸惡化,本堂神父常到家裡來送聖體,她對聖體極為尊敬,會花上一段時間準備心靈,穿著整齊,在小圓桌上舖換乾淨的桌布,並擺上蠟燭及花卉。幾年之後,祖母中風,行動不便之外,也無法言語。 在文冬主徒會會院望會半年後,我返家小住幾天。坐在輪椅上的祖母,看到許久未曾回來的我就眼淚直流。也許是不明白原本常在家的我,為何那麼久不曾出現?第二天清早,祖母極度不安,在我的帶領下,祖母竟能開口念經。她和我齊聲念完一遍天主經和十遍聖母經後,隨即恢復平靜。 幾個小時之後,祖母就與世長辭了。同年,我前往台灣進入陽明山初學院,以後接著到碧岳神學院念哲學與神學。晉鐸後,有幾年的農曆新年我在馬六甲會院,因此特意在除夕回家過夜。大年初一清早,依照家裡的傳統,家人一起在大廳念完〈新年經〉,拜謝天主後才享用早餐。 隨著時光巨輪的推進,阿依沙叻教友村也起了很大的變化,但祖父淡泊的胸襟、祖母慈祥的風範,依然留在我的心裡;而阿依沙叻這一塊孕育信仰的土地,縱然再遙遠,她的溫情,依然溫暖我心。 三、為人師表的導引 阿依沙叻村子裡沒有中學,華文小學的學生畢業後,都轉往馬六甲市區的公教中學或聖母女中繼續學業。小學六年級下半年,級任老師一邊為我們填寫升初中的表格,一邊問起同學們的未來志願。我一向對老師的工作感到敬佩,又剛在幾天前聽同學說,有一個修會是以教書作為傳教方法的修士團體,就順口回答說:「老師,我要當修士!」黃級任老師是位教友,他很驚訝地看著我說:「你要當修士,怎麼不早點說?要當修士的話,是要去八打靈的公教中學,不是馬六甲的公教中學!」 我坦誠表示還沒來得及和父母親商量,不知道他們是否會同意?黃老師答應這事就由他來處理好了,後來,他和另一位教友林老師親自到家裡來,向我的父母親提及我想當修士的事,並表示他們也支持我、鼓勵我。我的父親表示既然老師認為好,他也樂於同意;但我的母親則有點替我擔心,不知我那麼早就做決定是否適宜?先是兩位老師替我開了口,以後又有堂姐替我說項,不久之後,母親也就同意了。在黃老師的協助下,聖母昆仲會的初試院接受我的申請,同時也辦好了轉學手續。 天主安排了優良的老師,以言以行使我對教職有了憧憬,以後又透過我的同學,告訴了我有關教書修士的事;就連向父母親說明修道意願的人選,天主也都一一為我準備好了。 原本在純樸鄉間生活的我,一直循著村子的步調過生活;沒想到天主在我十二歲那年,為我開啟了另一扇門。新學年伊始,我已身處繁華的大都會,在八打靈的公教中學就讀,並住在聖母昆仲會的聖若瑟初試院。張春隆修士是一位經驗豐富的院長,知道如何諄諄善導。在他的帶領及薰陶下,四十來位中學年齡的修生,無論是學業或是品德,都有了長足的進步。 聖若瑟初試院也可以被稱為「修生的宿舍」及「未來修士的訓練中心」。除了和一般的學生一樣上課讀書之外,更有固定的時間來進行祈禱、運動以及勞作。在規律化的要求下,生活中仍不失年輕人應有的彈性與磨練。不論是排球、籃球、乒乓、羽毛球,還是各種棋類,都是我們運動及休閒時的最愛。除了養雞、餵豬、趕鴨、牧羊,連宰殺牲畜都可以不假他人之手。像這樣的陶成與訓練,的確造就了許多自主性很高、能力很強以及允文允武的修道人。 我在聖若瑟初試院住了六年,雖然後來沒能當上老師,也當不成聖母昆仲會修士,但我的團體觀念與靈修基礎,就在此時開始成長與茁壯,使得我往後的團體生活與修道生活受益匪淺。 離開聖若瑟初試院後,我返回阿依沙叻,並在堂區協助帶領青年活動,又在要理班服務。我懷著感恩的心,以實際的行動來回饋教會所給予我的培育。一年後,我申請進入主徒會,並在文冬會院望會;天主又為我開啟了另一扇新門,讓我在主徒會繼續修道的生活。 正因為有良師的引導,同伴的扶持,這一條修道聖召的路程,才得以延續。一路走來,我的獻身生活雖然質樸平凡,但也充滿色彩、感恩與喜樂。 四、文化福傳的力量 主徒會以「文 其實「文化」涵蓋了人類生活的所有層面。從文字、語言、政治、飲食、娛樂、藝術、建築物、人與人之間的互動模式……甚至敬神的禮儀等,莫不都與文化有關。面對數碼化的世代,我們要如何讓人了解文化的重要,進而透過文化來傳教?我們該如何塑造本身的人文素養,進而使自己成為傳教時言行一致的有效載具? 在我要入小學前,一向懂得和兒女溝通的父親,讓我自己選擇所要就讀的小學。當時,阿依沙叻村內有兩所教會小學,華文小學及英文小學各一所。我的大哥及大姐所讀的是英文小學,按理說,我只要跟在大哥大姐之後進入同一間小學就可以了,但我卻選擇了華文小學。 七歲那一年的決定,使我有機會先熟悉本身的母語與文化,為我後來成為主徒會士舖平了路。為華人傳福音的主徒會強調「文化傳教」,這也成了我後來積極投身於文化福傳的事工。 從小就只在村子內活動的我,極少有機會接觸到課外書。但就在我小學五年級的那一年,學校設了小小的圖書館,喜愛閱讀的我,很快就把所有的書都翻閱了。中學時期,所住的聖母昆仲會初試院有許多藏書,除了教會書籍外,我又有機會瀏覽多部中國名著。 以後到台灣念哲學與神學時,大修院允許修士每週四下午外出。那段時光,我常是在書店裡度過,連續好幾個小時站著看書也不覺得疲倦。晉鐸後修會的工作接踵而來,為了配合修會整體的需要,去深造的事一再延宕;但進修、充電的步伐那能停下來?因此,我添購了不少的書籍,並利用時間用心自修,來自我提昇。 這一場不斷提昇的過程,也反應在每一位主徒會士對文化傳教的努力上:「頭頭是道,以文化眾」。透過這短短的標語,主徒會所要表達的就是:「耶穌基督是道路、真理和生命。祂是教會的頭,我們是祂的肢體。我們願意透過文化來傳教,教化眾人去接受,並相信耶穌基督是人類的救主。」 為了要達成這樣的使命,主徒會在馬來西亞服務的會士,在八打靈聖依納爵堂、文冬耶穌聖心堂、芥子福音傳播中心、剛恆毅研究中心及主徒會馬六甲培訓院等地組成工作團隊,持續地發揮「文化傳教」的精神,一步一腳印,設法在馬來西亞編織一張「文化網」,為能取得更多的漁獲。 而「傳教」,就是向尚未認識及還未接受耶穌基督的人,「宣講耶穌基督的福音」。要讓一個非基督徒可以接受、並相信耶穌基督是救主,有時單靠傳福音者的「聖德」還不足於達成,往往也應該有文化面的「學識」作為催化劑。透過傳教對象所熟悉的語言、習俗、音樂、知識、人際互動模式、生活習慣等,基督的福音可以不再是那麼的遙不可及。 因此,傳教者本身的學者身份以及在社會上所取得的地位,都會有加分的作用,成為傳播福音的有效工具。如此看來,主徒會對於文化福傳的重視與耕耘,自有其一定的道理。 父親讓我在七歲那一年有機會決定自己的未來,不也展現了他對自己兒子的信任與尊重?他所展現的風範,縱然沒有學術上的考量,卻也造就了一位文化福傳的耕耘者!而我們身為傳教士,不也更應該對「每一個人」與「人類的文化」展現更大的信任與尊重? ﹙全文完﹚